台東都蘭藝術聚落故事
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蔡政良——流動的認同,成為多種可能性的人
1971年次的蔡政良,出生成長於新竹,人稱阿良。自述「個人認同流動於新竹客家人與臺東阿美族之間」。他和都蘭結下一生的緣分早於大部分藝文新移民,融入都蘭部落的程度更是自古以來的移居者中最深的。
從一個來做社群文化田野調查的研究生,到加入部落年齡階級,舉家遷移落戶,成為輔佐Kakita’an(部落領袖)的總幹事(相當於都蘭國行政院長的角色)…同時是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的教授、人類學家、紀錄片導演、民族誌影展策展人,甚至也以其錄像作品參與過2019年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及幾次當代藝術展覽。多重跨界的身分在每個他參與的領域都是非典型的「怪咖」,卻又都實踐得有聲有色。
初見都蘭就被灌醉了,立下誓約
阿良第一次到都蘭,是1994年他剛從大學畢業的那個夏天。90年代全臺灣各鄉鎮都在「社區總體營造」氛圍下,各地有許多地方文史工作室,阿良看見臺北山水客文史工作室在報紙上招募有志青年參與臺東都蘭部落的短期田野調查,剛剛考上教育科技研究所的他報名參加,並在工作室分配觀察任務時提出「我想看部落的教育」。他提前出發,一路從臺北騎單車下來,恰逢七月中旬東海岸阿美族的年祭期,經過東河部落時,先去看了東河的祭典,還有約40個Pakarongay青少年參加,騎到都蘭也正在Kiloma’an收穫祭,卻發現不但青年非常少,Pakarongay更是沒半個,這引發了他強烈的好奇。而當其他隊員搭乘遊覽車來到與阿良會合之後,他們被安排的住宿地點,是位於部落背後都蘭山腰上的「土地銀行招待所」,阿良在這個座山面海的建築陽台上,第一次見識到都蘭部落、都蘭灣與綠島連成一片壯闊無垠的美景,深深覺得一路騎單車那麼遠實在太值得了!而他當然無法預料,這個空間在十年後,被筆者的「女妖在說畫藝廊」認養承租,成為都蘭藝文匯聚與發散的有機平台。
初次來到都蘭的田野過程中,阿良認識了當時最年輕的「拉中華」階級的級長阿泰,因為兵役、工作、人口外流…等等原因那年回來參加祭典的「拉中華」成員只有阿泰跟另一個阿共兩人而已,非常單薄可憐,以致只能寄生在上一階的「拉贛駿」之中,連自己的集會所都沒有。而阿良的年紀也正好跟他們差不多,很快交上朋友,第一個晚上就被阿泰帶去某人家喝酒聊天,醉得無法騎車回住宿處,隔天早上在某戶人家的門口被阿嬤叫醒,問他是誰家的孩子?在那次田野中,阿良到處問人為什麼來參與祭典的年輕人和青少年那麼少?都蘭老人告訴他:「現在的家長們太保護孩子、不讓孩子吃苦,加上隔代教養、青壯年人口外流嚴重,因此沒有Pakarongay。」祭典結束之後,阿泰問阿良要不要加入「拉中華」?從此阿良開始了週五上完課,從淡水開九個小時的車下來都蘭,禮拜天再回臺北的六百公里奔波人生。
 蔡政良在1995年加入拉中橋,也協助都蘭部落振復Pakarongay訓練。
蔡政良在1995年加入拉中橋,也協助都蘭部落振復Pakarongay訓練。
那時候的Kakita’an是潘清文老頭目(族名Konui),和他的總幹事林正春(也是都蘭國中的老師)、鄉民代表黃金照正討論在現代的社會衝擊下要如何恢復過去的Pakarongay訓練,最後他們決定透過在都蘭國中辦理訓練營方式,由於沒有人來帶孩子,阿良邀來大學山地青年社的學生來幫忙。同時為了設計訓練營的內容,他不斷往返臺北與都蘭做許多田野調查,訪問部落仕紳、頭目、權力核心回溯過去Pakarongay訓練過程,整理資料重新設計課程,終於在1995年夏天辦理訓練營。
1995年夏天也是阿良正式加入「拉中橋」(老人家覺得拉中華不好聽,到底是講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大橋,因此在新的kapot「拉監察」成立時,也將「拉中華」改名為「拉中橋」)的第一年,他還沒有傳統服,只是跟著在旁邊見習「我也不曉得要幹嘛,他們叫我倒酒、搬椅子,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那一年祭典結束的時候,級長阿泰請阿良站起來自我介紹,並希望他可以年年都回來參加「拉中橋」,還把自己的「alosaisai」(披肩)送給他,阿良承諾一定會回來,並在那一刻起開始對都蘭有了歸屬感。自此以後每一年都蘭的Kiloma’an,阿良從未「休耕」過,就連後來服兵役也沒缺席,有一年趕回來參加祭典途中遇到車禍,他拿鐵絲把保險桿纏回去照樣開回來,只因為阿泰邀請他加入時說過:「不能缺席!」,並且阿泰自己就從來沒缺席過,就算老闆不放人他寧可自己放假丟工作也要回來。事實上當1996年夏季,阿良真的帶著準備好的全套傳統服出現在祭場,「拉中橋」的兄弟們非常驚訝,他們原以為阿良只是隨口答應,沒想到是認真的兌現承諾。「特別是我們並非土生土長的都蘭人,更加需要證明自己是認真的。」
成為真正的男人
在1995年協助都蘭部落振復Pakarongay訓練期間,潘清文老頭目想要給阿良一個阿美族的名字,本來要給阿良他自己的名字Konui,但頭目夫人不贊成,說那是酒鬼的名字(順便罵老公),反而給了阿良她弟弟的名字Fotol’,因當時的阿良仍不諳阿美語的書寫符號,因此陰錯陽差地以英文拼音的方式成了「Futuru」,Fotol’直譯是「睪丸」嚇得阿良瞬間酒醒,而老人家說這是一個好名字,象徵的是「真正的男人」,是老人家對他人格特質的判斷也是祝福。潘清文頭目於是狠狠地捏紅了阿良的耳朵,宣布從此以後他就是Fotol’了。過去傳統上命名時是要被捏耳朵捏到哭出來的,後來阿良才了解,都蘭阿美族許多文化習俗和傳說都跟耳朵有關,小米神也是從耳朵跑出來的,他認為「聽覺是阿美族重要的靈魂通道。」有人說命名是人一生中聽到的第一個咒語,而阿良的阿美人生第一個咒語即是「成為真正的男人」!
後來阿良1999年退伍之後,便進入竹科工作了四年,負責電子數位學習的開發設計,結了婚孩子也出生了,但他始終很想真正搬到都蘭生活,可是考量自己不會種田、抓魚,剩下教書貌似是可以在臺東生存下來的方式,於是決定去唸博士班,並且選擇了他完全得從零開始的人類學,為此他竹科的老闆覺得這年輕人瘋了,苦勸未果還自動提出給他一年的時間,停職留三分之一薪水去試試。2003年順利考上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後,他有半年的時間可以待在都蘭,住在都蘭的義父林昌明家裡一起生活。之前1995年來都蘭辦Pakarongay訓練營期間,那批青少年的級長林一凡帶阿良回家洗澡,一凡的爸爸林昌明和洛恩阿公便叫阿良在家裡住,結下緣分,加上後來經常來訪,每當有人問「這個年輕人是誰?」林昌明都回答:「我的乾兒子」,最後連遠嫁回娘家的姑姑們也自然而然的接納了這個經常住在家裡的「ngay ngay」(喜歡用狀聲詞的阿美族人對客家人的暱稱,因客語nagy是「我」的意思,同時客家話聽起來有很多鼻音)。然而阿良真正深刻意識到自己是家族一份子,是在2005年,林一凡的阿嬤去世,蔡政良的名字被印在訃聞上,隔年親戚會的家族譜系榜上也列出他的名字,「才意識到成為了家族的一份子,責任義務連帶而來,不是說說而已。」
而在博班期間,他不只繼續以都蘭阿美族的生活文化為研究主題,最終在2010年完成博士論文畢業,回都蘭殺豬感謝部落族人;更持續從2001就開始的紀錄片發表,〈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2001)、〈阿美嘻哈〉(2005)、〈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新大洪水〉(2010),還出版了〈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一書。都蘭的祖靈是真的喜愛這個來自新竹的Futuru,阿良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立即獲得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的專任教職,立刻請太太和兒子一起搬來臺東,一家人正式在都蘭落戶定居了!
 兒子通過五年的pakarongnay考驗成為真正的男人_在石堆中開心的一家人_2021_李昶憲攝影。
兒子通過五年的pakarongnay考驗成為真正的男人_在石堆中開心的一家人_2021_李昶憲攝影。
喝風吃木頭的人~Isu-dit
在1995年初加入「拉中橋」時,跟著Kapot到上一級「拉贛駿」的集會所拜訪聽訓時,阿良就認識了那時剛剛從都市回到部落成立木雕工作室的Siki,以及他的老師拉黑子,還恰好見證了拉黑子送了一張漂流木的「頭目椅」給潘清文老頭目表示敬意。當時Siki在得知阿良受託協助恢復Pakalonay訓練時,還皺著眉質疑外地人阿良有什麼資格帶領部落的孩子?阿良回答:「事實是有資格者沒有辦法,沒資格者太過熱心,但我也希望明年就有部落的人可以帶領年輕人。」這番話也讓Siki深思,幾年後他也自動承擔起Pakalonay訓練的重責。而從相識那一晚起,一直堅持著文化精神探索與發揚的Siki,是阿良認識的第一個都蘭藝術家,也是他非常敬重的部落哥哥。
過了幾年,阿良退伍再回到都蘭時,發現越來越多特立獨行的藝文工作者來到都蘭,尤其是「意識部落」那一群跨各族的藝術家,以及「都蘭糖廠咖啡屋」的都市漢人藝術家。阿良對於這群人第一印象是「很酷」,因為以前在臺北曾是河左岸劇團的團員,「怪人看了許多,但這些人更怪,這樣也可以活下來哦?」雖然對於這些藝術家群體感到好奇,但是因為他在都蘭的生活圈還是以部落為主軸,慢慢的發現這些藝術家與部落沒有太核心的交集,唯一的交集大概就是Siki,藝文新移民若想邀請部落老人家參活動與或協助祈福,都是透過Siki去溝通邀請。「若部落是一個較為穩定的存在,Siki是媒介,而其他藝術家是跨越邊界,在邊界裡游離的人。臺灣原住民已經是臺灣主流社會蠻邊緣的群體,但這群藝術家又是更邊緣游離的一群人。」
而都蘭糖廠因為「糖廠咖啡屋」營業被打開後,阿良偶爾會到咖啡屋裡感受他稱之為「波西米亞風怪咖群聚的世界」,也聽到部落人對糖廠這群不修邊幅、拓落不羈的人之看法,最廣為流傳的是Siki媽媽的形容:「這群人都是髒兮兮的藝術家,喝風吃木頭就能活喔?」在阿美語中「Makadit」是髒兮兮的意思,老人家創了一個新詞「Isu-dit」(藝術音譯結合髒兮兮的意思)來形容「好像是一群不事生產、也沒在海邊採集捕魚,每天都在刻木頭的人。」
 阿良佩服既核心又邊緣充滿流動性的Siki哥哥。
阿良佩服既核心又邊緣充滿流動性的Siki哥哥。
然而藝術新移民群體的出現,雖然為部落帶來新的刺激與文化的流動,但隨著藝文活動的蓬勃發展,也引來各方對原本寧靜的都蘭之關注和不同目的的慾望投射。2000年過後,臺灣對東部的發展政策走進觀光產業,開始出現BOT等條例,在整個氛圍下,如作家舒國治描寫都蘭糖廠咖啡屋的文章〈台灣最遠的咖啡館〉、前總統夫人周美青背著都蘭國小的書包,以及後來與美麗灣對抗事件都已經進入全國版面,都蘭成為一個投射想像的聚集地,同時都蘭房價、租金與地價飆漲,成為轉捩點。都蘭糖廠的氛圍也不一樣了,最顯著的改變是自從小馬、小竹將「糖廠咖啡屋」轉手給新的資本家後,阿良自己就很少再進去那空間。就連「意識部落」藝術家們也紛紛把重心轉往他處,隱身在自己的工作室,從都蘭為核心向外漫開,各自根據。而糖廠也漸漸轉向分租給不同的單位,更多元的屬性與經營方式,例如拉黑子租的倉庫作為自己不對外開放的創作工作室,鬧中取靜;豆豆兼具展場與文創展售屬性的二倉工作室;敏書的台11酒寮也發展出讓更年輕一代的「文創移居者」,藉由假日市集群聚共生的環境……阿良認為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情況,但是沒有太大改變的是,糖廠依舊是外於部落族人生活領域的空間,「我聽Siki說過大部分的老人家們對糖廠的不好經驗,過去在糖廠工作時,曾經被苛待或受過傷,因此不太敢接近糖廠。」
阿良早在2012年就將上述觀察寫成一篇〈臺灣東村?〉的文章,他以紐約東村來類比2000年後的都蘭,「在曼哈頓區有個東村,約自1950年代開始便是各種另類與波西米亞式藝術家、嬉皮、龐克,與各式各樣藝術、地下電影,音樂,報刊與前衛社會運動者匯集的區域。然而,隨著另類藝術的發展,卻弔詭地形成一種時尚風潮,大批的富人嗅到時尚帶來的商機開始炒作房地產,使得房租地價快速上漲,另類的藝術社群、便宜的獨立書店與咖啡店消解,東村進一步被同質化,不再存有過往生猛活力的邊緣性格。」從本來是根本沒有人要居住的邊緣之處,因為各種邊緣人的進駐,尤其是渲染力極強的各類藝術家,變成很酷的地方,吸引了人潮來尋找奇觀,形成商機之後,更大的資本吞噬就來了,於是很酷的地方變成沒人住得起,邊緣的人又需要再撤退到更邊緣的地方,譬如現在雙濱地區。然而部落的人更慘,倘若因為一時家裡經濟問題把土地賣掉,就根本再也買不回來,只能永遠「旅外」了!
時隔十年,阿良認為都蘭的臺灣東村模式只有更清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談,是從都蘭擴散出去,而都蘭的獨特性始終無法被取代,這個獨特性在於「都蘭的原住民族主體性蠻強的,不會因為有錢的、浪漫的、靈修禪修的人進駐後,太過改變自己的主體,不會去附和這些人或要把對方拉進來,意思是各過各的生活,過好自己的。」他舉例部落近年為了將傳統領域收回,以及讓返鄉的部落青年能夠在自己的土地安身立命而發展的「都蘭國」計畫,其實就是都蘭部落主體性的實踐,部落青年曾經找這些開設民宿、文創、衝浪店、咖啡館、餐廳……的新移民談合作,目前在都蘭最夯的餐飲業者,來自西班牙的某店家老闆就說:「為什麼?這裡應該是大家的,而非部落的。」阿良笑著說,他的祖先也是這樣的,從16、17世紀到現在沒有改變,若他沒有理解自己祖先的侵略,「那就算了,好來好去就好。我們以部落為主體的概念,有些人不願意參與、有些人則是找不到管道、頻率與部落對話,難說好或壞,只要部落的主體性還在,慢慢的把外面願意加入的人拉進來,而非屏除在外,部落就會越來越強。」前提是不動搖部落的主體、不消費部落,部落的人就會尊重他在這裡的生活,阿良其實經常提醒自己也是外來者,只是可能比大家都早一點來而已。
 阿良帶著乾爹林昌明和弟弟林一凡到新幾內亞踏訪阿公當年當高砂義勇軍走過的叢林土地並拍成紀錄片_2009_莫三比克河上。
阿良帶著乾爹林昌明和弟弟林一凡到新幾內亞踏訪阿公當年當高砂義勇軍走過的叢林土地並拍成紀錄片_2009_莫三比克河上。
屬地主義的認同——Settler的自我省思
關於自己也是外來的移居者這一點,阿良認為我們都是「Settler」,「要看是在什麼脈絡下談論這一詞,若以原來就住在這裡的人而言,相對而言後來者都是Settler,可是以原住民來講『Settler』是墾殖者,『Settler colonialism』中文翻譯以定居者殖民主義,非原住民的學術界在講『定居者殖民主義』,我認為是自我安慰、自我除罪的翻譯,因此我會以『墾殖者殖民主義』解釋該詞。以現在時代的大都市來說,就像當時三鶯部落或溪洲部落,他們對馬英九而言是移民者,執政者認為這裡是都市地帶,原住民應該待在部落卻侵佔了河川地,在政策與法令上就將其當作Settler來看待,這時候又不能將Settler一詞翻譯為墾殖者。在不同的脈絡底下會有不同的詮釋。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Settler,但我不以墾殖為目標。我自己認為不管是哪種型態的Settler都要的第一個前提是,要考量部落願不願意讓你加入,第二是若能成員原住民族群的一份子,經過兩三代以後就會成為Community Member;但有些人如果只是來到這裡卻不願意加入社群,那就始終只是一種墾殖者。」也就是說,即使阿良已經變成Futuru將近三十年,也確定自己將在這裡終老,但他仍然很清楚自己對於部落族人而言很多時候還是在「Settler」與「Member」之間游移,我們或許都要經過兩三代之後,才能成為真正的「Member」。
特別是,在阿美族社群文化是老人政治,都蘭Kakita’an的年紀通常落在60~65歲,他的國策顧問團年紀更大,阿良雖然以移居者身份擔任總幹事這麼核心的位置跌破大家眼鏡,但其實在第一年就感受到老人政治的情況,「擔任總幹事的期間有感受到,原來部落有許多人還是把我當成外來者的角色,但擔任總幹事這幾年下來,有發現自己被看待的方式從『Settler』慢慢變成『Member』了!」
那麼都蘭部落為什麼如此特別?可以在吸納如此多元的差異之後,依然保有自己強盛的主體性?阿良概略分析了都蘭的人口組成與遷移史,提到都蘭部落其實本來就是移居者組成的群體,其中有一群人稱為「Palilaw」,是來自恆春的人,「Palilaw有兩種意涵,一種是本身就是阿美族,有些則是平埔族。」也有祖先是卑南族的家族,以及從馬蘭移居的阿美族……因此,阿良認為在都蘭阿美族人對於「Niyaro’」(部落)的認同中,「屬地主義」遠比「民族主義」重要,「所有事情要維持『純種』是非常困難的,走到純種的概念會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就像納粹。」此外從地理環境來看,都蘭從山到海的腹地相對夠大,南北皆有河流,距離台東平原又近,確實是吸引地靈人傑的豐饒之處,從清朝胡鐵花上呈朝廷的報告,就知道都蘭是僅次於臺東平原馬蘭的人口第二大的部落,那時就已經達到約1500人左右,比部落人口大量外移的現在(約1200人)還多。
 導演蔡政良的神情_李昶憲攝影。
導演蔡政良的神情_李昶憲攝影。
流動的認同與其能動性
阿良也以自己為例,「我希望自己是流動的、多種可能性的人而非被定位的。」他對都蘭部落的成員有認同,對所屬的「拉中橋(Lakayakay)」kapot有深刻的認同,但對自己的社會性身份、位置就保持流動的認同。譬如他不會去問自己是一個人類學家嗎?這是受到過去博士班的指導老師James的影響,每當他看到阿良的文章寫「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他總是反問:「你先告訴我什麼是人類學的角度?你要面對的是一個問題、現象,而你想去回應,但這問題只能用人類學才能回答嗎?」他認為人類學不是可以被定義成一個特定的、想像式的答案,「我們要面對的是不斷變動的社會文化現象,他認為人類學應該是要開放式,而非設定一個Frame work。」因此阿良看待認同這件事越來越彈性了,因為「看到在邊緣的好處。」
因此回頭再看這二十年來來來去去或移居在都蘭一帶的「Isu-dit」,阿良認為每個社群都有流動的存在,若社群具有創造力的是邊緣的這群人,他們的創作會傳遞到內部讓社群有往前走的動力,「但若這群人根本只是在周遭,也不提供任何有關洞見的行動,對我來講只是肥料。藝術有其能動性,確實能提供洞見,但其能動性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直觀,而是創造出一種看不見的氛圍與力量。」不是從好壞來談,而是這樣一群人確實創造了某種可能性,那可能性到底是什麼?也許是動力?「若社群太強到每個人各司其職就太過僵化,甚至是一種霸權。我認為藝術創作者是需要不斷的反省,因為在的位置有時在邊緣、有時在核心,是一直不停在移動的,跨越邊界的能力是創造力的來源與可能性,我也覺得他們在這樣的地方提供了一個動力。」
 蔡政良作品《返潮彼時的生與死》_2020台東美術館邊界都蘭展。
蔡政良作品《返潮彼時的生與死》_2020台東美術館邊界都蘭展。
2019年筆者策展的東海岸大地藝術節,邀請都蘭部落的Siki、阿良和來自美國的DJ Hatfield(施永德)三位截然不同背景,但都生活在都蘭部落脈絡中的藝術家共同創作,阿良這次協槓了藝術創作者的身份。在討論創作主題與如何合作時,Siki提出了一個只有在阿美語境才有的奇妙詞彙「Masi’ac」,阿美族人用來指稱漲潮與退潮交替的奇妙時刻,立刻獲得兩位人類學背景的「settler」創作者熱烈回響,最後阿良以其影像作品描述:「對海岸地區的阿美族人與海洋的關係非常密切,人與海洋形成一種互相定義的存在。其中,潮間帶更是阿美族人與海洋之間互動的空間,在潮來潮往之間,有一個用中文無法描述的潮水階段,阿美族語稱為masia’c,亦即海水在開始要退潮時,到某個階段,趁滿潮來潮間帶覓食的魚群開始出現慌亂的狀態,而此時也是阿美族人趁機撒網捕魚的好時機。海裡的魚,因為求生來到潮間帶,卻也可能致死;阿美族人來到潮間帶,是個求生的賭注,把滿懷盼望的網撒出去,不是魚死,就是人活。masia’c基本上就是一個交織著各種生命與死亡、機會與運氣、興奮與失落的一個大型海洋賭場,部落位於支配社會的邊陲,與都會之間宛若潮間帶與大海之間的關係,在都會海洋中的族人們,在某個特定季節紛紛湧入部落潮間帶吸取文化養分,時間到了,又紛紛地離去回到都市的海洋。是的,有些年輕人被文化的陷阱困住,留下來了,但是,這些留在潮間帶的年輕人,到底是會活下來?還是會慢慢地死去?」
 蔡政良作品《返潮彼時的生與死》_2021羅東文化工場展出_攝影 吳欣穎。
蔡政良作品《返潮彼時的生與死》_2021羅東文化工場展出_攝影 吳欣穎。
「Masi’ac」象徵著一種充滿機會同時也充滿危險的生存狀態,也是都蘭阿美族族面對海洋的流動、循環、毀滅、不定形、包容各種差異等特質的生存美學。來自一個「身土不二」的族群文化,阿良如何面對海洋民族永遠處於「Masi’ac」的靈活流動狀態?阿良說念人類學的好處是:「沒有真正本質化的東西,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但在變化的過程裡,有一些事情還是得守住,「關於階級(Class)、主體,以社會學馬克思所述的階級會牽涉到權力,宰制者與被宰制者之間要看得清楚,在社會裡階級之間的壓迫還是蠻嚴重的。」這也是為什麼初見的人總是難以置信看起來比較像流氓或工頭的阿良其實是大學教授,因為「教授在社會裡也是一個資本,已經被定型「應該有的樣子」,我認為這是應該要被打破的。」
同時,「邊緣不能變成姿態,若邊緣成為姿態或太過做作,流動性則會不清。」阿良很佩服Siki,在部落中可以很核心又可以退得很邊緣,Siki的流動性很強大。對於認同這件事情,「我希望自己是流動的,成為同時有多種可能性的人。若真要問我是誰,我是Ngay-mis!Ngayngay ato Amis sanay!」
文章摘自 《紮根於流動中的邊界敘事—臺東都蘭藝術聚落故事》(圖左)、《紮根於流動中的邊界敘事II臺東都蘭藝術聚落故事》(圖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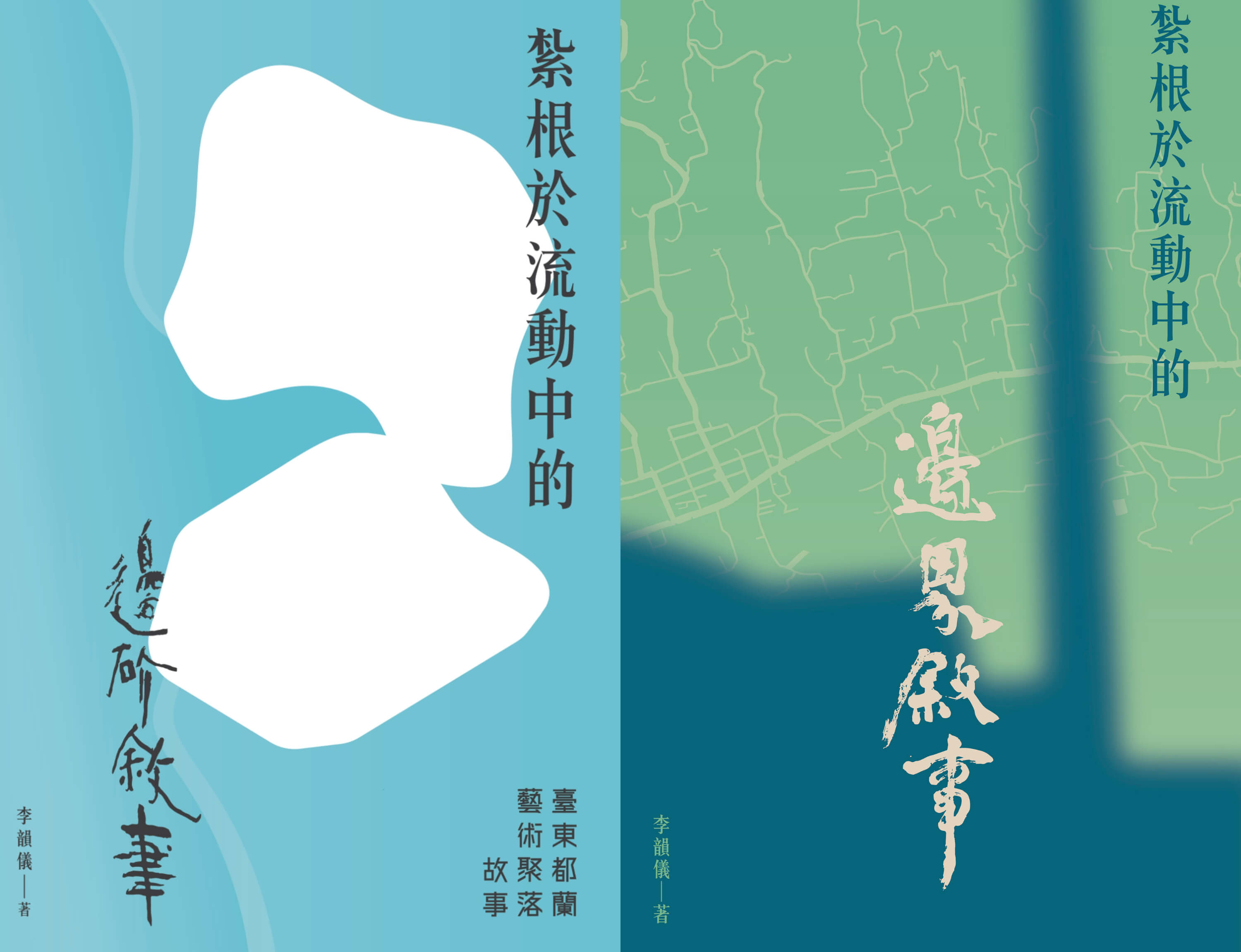
出版|臺東縣政府
作者|李韻儀
作者李韻儀以臺東都蘭女妖在說畫藝廊為基地在東海岸從事策展、藝術書寫二十年,在2022年與2024年分別出版「都蘭藝術聚落故事」,透過訪談以及筆者自身與受訪者多年相濡以沫之理解,書寫各種不同領域、背景與路徑卻相繼選擇「都蘭」作為安身立命之處的跨世代、跨領域藝文工作者之故事。
《紮根於流動中的邊界敘事——臺東都蘭藝術聚落故事》為出生於台北,就讀於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並移居都蘭二十餘年的李韻儀所書寫,在首部曲和續集中集結了52篇人物故事,記錄都蘭在地部落耆老和藝術家、新舊藝文移居者的在地觀點與個人故事,並涵蓋短居卻深刻影響在地的已故藝術家。 如續集在序言中引述自夏黎明的《文化研究月報》第66期〈都蘭:流浪他方的故事〉,本書是為了探問「都蘭從1990年代中期至今,如何從島國東陲的阿美族村落,蛻變成文化研究者眼中『無可替代的…地理想像』」。全書以人物訪談為基礎交織作者觀察,呈顯出作者與藝術家們「生命交融的對話」,也透過引述故事主角的話語為本書讀者形塑出與藝術家對話之感。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