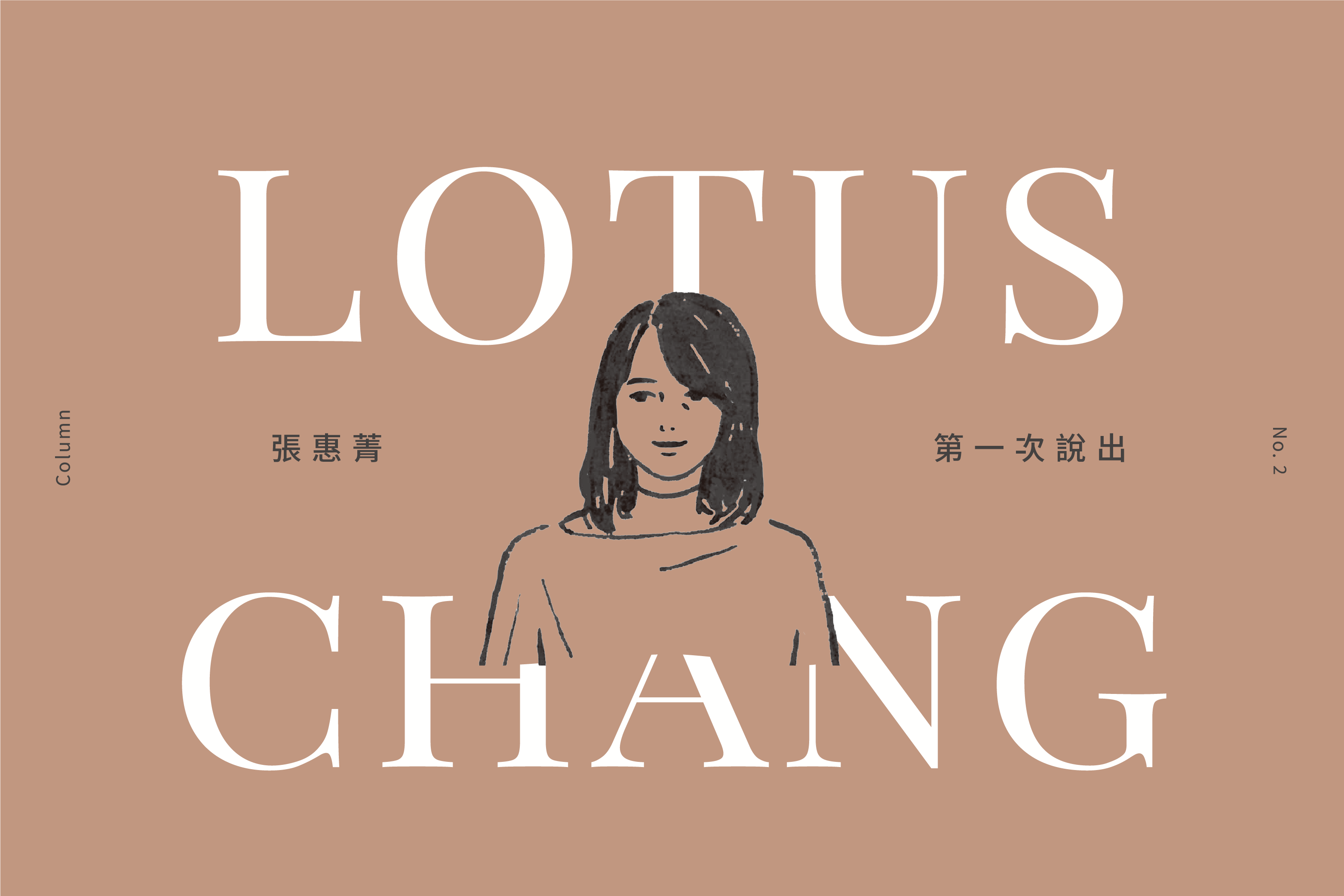張惠菁:第一次說出
No.2 逃跑的世代,與用逃跑路線繪成的地圖
「我是啊,一直在逃,直到我漸漸能夠感到,逃跑也是在繪製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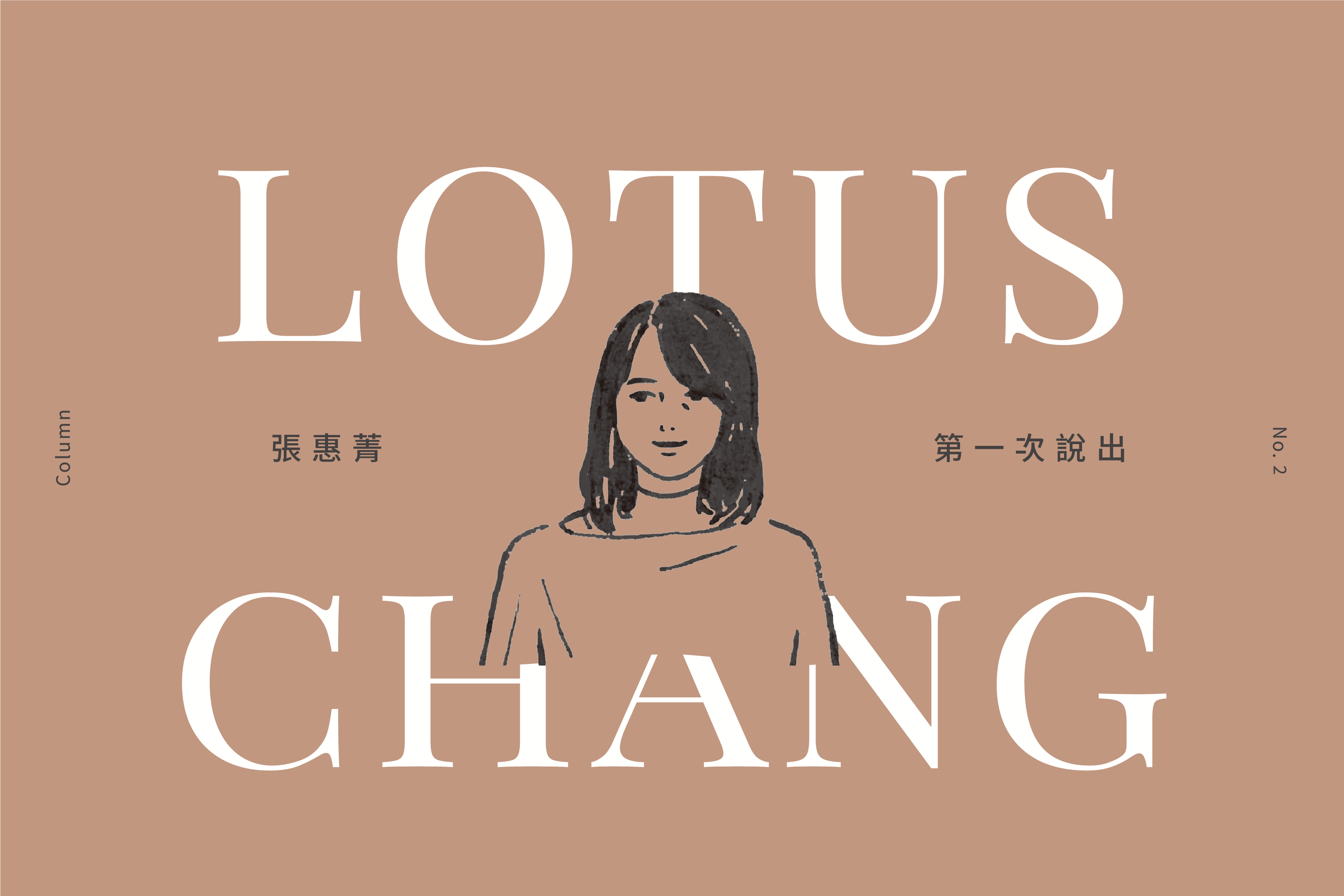
「我們是逃跑的世代嗎?」有一天,W 在我們的朋友群組裡問了這個問題。
引起她這個問題的,是黃麗群為台積電文學獎寫的評審講評:「我們這一代對父母的大主題是『逃』,等到我們接棒,努力成為『不讓小孩想逃』的開明父母,但子女想緊緊攀住你時你又因形格勢禁無能為力,或甚至,根本不曾想過子女並非像自己一樣『不想黏著父母』,反而是懂事地不敢黏著你、不敢說出『我想黏著你』因為怕讓你為難。」這段話是黃麗群對著去年散文首獎〈重慶印象〉而說。
黃麗群所指的「我們這一代」,大約就是包括我在內的六年級。我們這個世代與父母的關係之所以是「逃」,在我看來恐怕是有一種時代整體的緣故在裡面。我們的父母親是各種各樣的「移民」第一代,從鄉到城,從中國到台灣,母語到國語的移民。有可能是家裡第一位上班的女性,或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板塊劇烈移動,外在環境有一個主述的集體敘事(如戒嚴、經濟起飛);每個個人的經驗雖非常不同,卻未必有語言可以對應那不同。話語經常還是從大環境借用的,類型化高過個體感。
我母親在引用民間諺語教我道理的時候,經常加上這麼一句「不然怎麼會有這句話」。要說服她採納另一種道理,需要拿出成立的「類型」,讓她能類比、掂量,更好的情況是讓她能重新做價值排序。不過,這是我很久以後才明白的事。在早年,我只能繞路而行。「我們是逃跑的世代嗎?」我對這個問題太過百感交集。
我是啊,一直在逃,直到我漸漸能夠感到,逃跑也是在繪製地圖。
當我讀到漢德克的《夢外之悲》如何寫他的母親時,雖然是那麼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地域經驗,卻覺得有一點共鳴:在歷史之中,夾在劇烈移動的板塊之間,一個小人物已知的語言難以完全表述自身,他怎樣理解與體驗自己的個體性?漢德克不急著描寫他母親如何與眾不同,反而是從「匿名的集體」反過來寫她。「人們在自己的意識中,看見自己所做的動作同時被其他無數的人重複著,於是這些動作形成一種運動的節奏—生活也藉此得到一種既被保護且又自由的形式。」這是從鄉間到城市工作,剛開始獲得一點個體感,立刻又被整理進國家集體裡的,漢德克母親的臉孔。
台灣的經驗不同於奧地利。我們父母親世代的語言,比漢德克願意在母親身上回想起來的,更豐富些。但父母親的世界也幾乎都是「折疊」過的(此處借用朱嘉漢小說裡的用詞—「折疊」)。往內折起一種母語,一種鄉音,一些沒有實用作用的好惡,好與外界集體齊平地相接。他們從折疊起來的形狀往外看,也把那些觀察所得投射給我們。所謂我們這一代對父母的「逃」,我以為,是在逃離那個折疊過的世界觀。雖然無法開口說他們錯,但一時無法勸阻他們慣性的折疊。且憑經驗知道,若靠得太近,那折疊便會被加到自己身上來。
於是盡可能遠離,不折疊自己,不折疊他人,在各種人際關係上盡量「不讓人想逃」。保持著相當有禮的疏離。幸而,在我們成年之後,時代漸漸在展開。
閱讀朱嘉漢《裡面的裡面》就有這樣的感覺,時代繼續在展開,一個關於他曾祖輩、祖輩先人的故事被小說家展開出來了。他們當中有人曾經加入台灣共產黨,有人在中國擔任通譯,有人留學日本,有人先學習成為護士後來又做貿易。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第一代(家族中第一個留日、第一個去中國、第一個逃亡⋯⋯),但是留下來的敘事卻少得不成比例。朱嘉漢的寫法,他用不斷向內摺紙般的、內向的語言來寫,是看見其中有太多失語、失憶,但並不試圖用想像填補全部。他展開他們的折疊,但保留著,其中乃有失語和失憶,是我們必須尊重、面對的。
那並不是與今天斷裂的歷史、完全在我們身外的故事。我們也有自己的失語和失憶時刻。對我而言,我閱讀《裡面的裡面》的方式,是讓它提醒了我,在我自身周遭也還有許多空白。

張惠菁
台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碩士。1998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流浪在海綿城市》,其後陸續發表有小說集《惡寒》與《末日早晨》,及《閉上眼睛數到十》、《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步行書》、《雙城通訊》、《比霧更深的地方》等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