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改變了,一切也都沒有改變」:何偉與他的中國書寫
美國作家、紐約客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是長期書寫中國的西方作家宗最特別的一位。自 2001 年出版《江城》(River Town)以來,到最新作品《別江》(Other Rivers),他從日常角度記錄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社會變遷、城市發展、教育制度與世代差異。本文討論他二十多年來的書寫,並特別聚焦《別江》中對疫情時刻與習近平時代年輕世代。雖然他的中國書寫不是直接定義中國或者特別強調政治,但其實那個政治暗流是無所不在。
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中國夢」的偉大夢想尚未誕生,中國尚未「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網路世界(與監控)尚未覆蓋人們生活。一名年輕的美國人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以美國和平隊身份來到四川長江邊一個叫涪陵的小鎮,在師範學院作為一名英語老師。幾年後,他把這段時光的生活觀察寫成一本書《江城》(River Town,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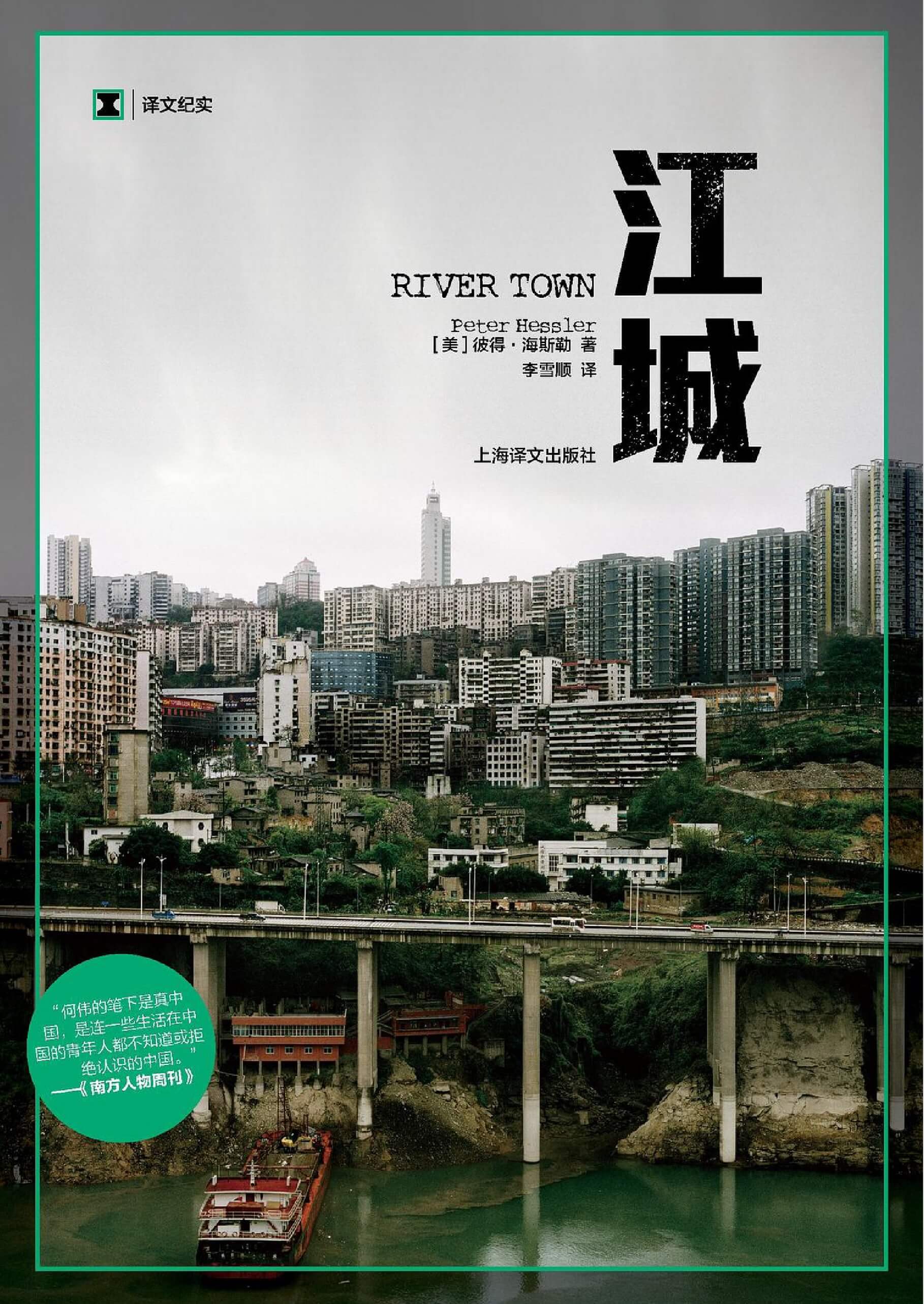
何偉寫作的特別在於他不是揭露中國黑暗面的調查報導,也不是帶著理論框架的研究著作。它只是耐心記錄一個外國年輕人如何在陌生的語言、制度與文化中觀看與傾聽,以一個根植於地方的切片,去理解那個劇烈變遷的巨大國度。
「我沒有興趣定義中國。我更有興趣的是人們如何生活,以及這些生活如何以微小的方式改變。」他說。
但他當初或許沒預期到,這本由外國人寫中國的書,不僅在台灣受到關注,更在中國出版中文版後成為一個文化現象。
二十多年後,何偉帶著家人重新回到中國教書與生活,並寫下新書《別江》(Other Rivers)。
從《江城》到《別江》,橫跨二十多年巨變的中國書寫,當然太多事物都不一樣了,但也有太多事物都沒改變。
在這條緩慢流動的敘事之河中,何偉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的生活在時間長流中的改變與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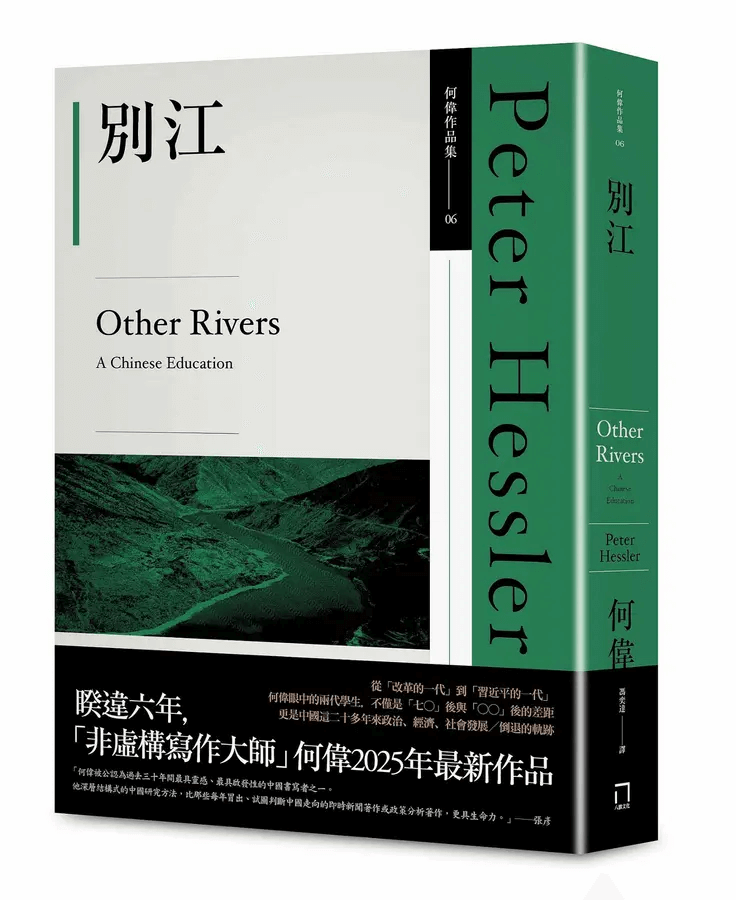
從《江城》開始的「微觀中國觀察」
1996 年,二十多歲的何偉抵達四川涪陵,這座沿江小城位於長江與烏江交會處,地勢陡峭、霧氣瀰漫、節奏緩慢。這裡不是世界關注中國的焦點。
他住進一間簡單的房間,在這裡教了兩年書,後來寫成《江城》。
他寫他的學生如何面對體制與對未來的希望,寫校園日常中的權力角力,寫街頭小販與出租車司機,也寫人們對於文革的沉默記憶。他察覺人們如何在歷史與政治的陰影下發展出高度自覺的語言策略,觀察制度如何以最細微的方式塑造行為。
《江城》不把中國當作一個抽象概念,而是在涪陵的街巷、學校、茶館中,在濕氣和河霧構成的空間裡,聽取人們細微的聲音,建立起九〇年代末一座中國小城生活的質地,及其如何面對歷史浪潮帶來的衝擊。
《江城》在中國獲得極大的反響,何偉成為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學生與年輕讀者熟知的名字,他的書甚至被當作理解改革開放世代的一種「非官方文本」。對許多中國讀者而言,《江城》並不因為是一部「外國人寫中國的書」而顯得失真,反而以一種不居高臨下,也不刻意批判的態度,替他們保存了一個正在迅速消失的年代。

從《甲骨文》到《尋路中國》:轉型時代的日常檔案
離開涪陵後,何偉進入《紐約客》擔任駐中國記者。2006年出版《甲骨文》(Oracle Bones, 2006)。這本書像一部橫跨三千年的時空剪輯:考古學家的追尋、維吾爾族學生的漂泊、農民工的遷移、語言學者的迷惘——都成為理解中國變動的入口。他用人物敘事串起政治、古史、語言與城市擴張,而非用結論強行解釋世界。
接著出版的《尋路中國:長城、鄉村、工廠,一段見證與觀察的紀程》(Country Driving)(2010),則宛若一部當代中國的公路片。他開車穿越北方村鎮與南方工業區,跟著農民工、汽車代理商、創業家庭走過中國經濟的野蠻生長,寫那些在「成功」敘事背後,被速度與競爭不斷推擠的人們。
這兩本書構成了世紀末轉折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快速崛起的「日常記錄」。書裡沒有「典型中國人」,只有具體的人:這些人物不承擔象徵意義,卻在長時間的累積中,構成一幅幅豐富立體的社會圖像。
其後,他和家人移居埃及,繼續為《紐約客》寫報導。2019年,他們一家回到四川的長江河邊,在成都的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而如今這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當然和上世紀末的中國完全不同了。他寫下新書《別江》(2024)。
《別江》:習一代的中國
當何偉回到涪陵探訪時,目睹最直觀的變化是:舊城消失了。
三峽大壩蓄水後,原本的江岸、老街與碼頭大多沉入水底。他必須依靠舊照片判斷,曾經站過的位置如今距離江面有多少公尺。
三峽大壩在 2000 年代啟動蓄水後,涪陵原本的江岸、老街、階梯與碼頭大多沉入水底;那些他在《江城》中寫下的路、樓、河岸角落、茶館、出租車站,如今都被新城區、住宅大樓、沿江公園、摩天大樓取代。

這種地貌似乎在,但地點消失的矛盾,是理解今日中國的錨點:城市快速更新,記憶無處安放,反映了中國二十年來深層的治理邏輯。
在《別江》中,他重新見到當年的學生與朋友,他們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快速變遷中各自走向不同的位置:有人進入體制獲得穩定,有人創業成功,也有人在競爭中被淘汰;更多人學會了如何不說多餘的話。這些命運交織成一整個世代的縮影。
他將教育作為打開整個社會結構的鑰匙。書中,他不僅描寫教育制度的運作,更透過學生、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互動,呈現一個社會如何在制度壓力、階級競爭與歷史記憶之間自我運轉。
他把他的學生稱為「習一代」,因為他們是在這位領導的權威下長大的。他說他九十年代的學生「都很天真青春」,因為他們要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但現在的學生成長於穩定繁榮的時代,卻面臨極其激烈的社會競爭(內捲)。他描述這一代學生有老靈魂:「他們曉得事情的道理,也了解體制的缺點,也了解體制的好處。」他們「對中國的體制沒有幻想。」
「沒有哪個虛構世界的設定,是把威權主義、審查制度和經濟成就、遷徙自由與教育提升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哪個小說家能料到,對一個鎮壓性國家來說,「競爭」竟然這麼好用」…….同學們最怕的是彼此——是其餘也在為分數與工作機會較勁的年輕人……我認識的中國年輕人,多半已經因為為了成功而拼搏,結果變得太麻木。」
他也把雙胞胎女兒送入當地公立小學,用許多段落描述小學教育的紀律、競爭、死背和許多荒謬的課本或考題,如何讓他驚訝。
2020年初,疫情來了。何偉一家人經歷了這個奇異的時刻。《別江》因此也是一部疫情時期的中國日常誌。
一切控制與封鎖都具體而細密地刻在個人經驗裡:鄰居在大廈裡收到一台幾乎放不進電梯的大型電視;被困在宿舍的學生依靠機器人送外賣;即使成都的措施遠不如武漢那般嚴酷,但每個人仍被迫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
疫情也改變了何偉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距離。隨著封控升級、加上中美關係急速惡化,外國記者逐步被驅離或限制活動,和平隊項目也因政治壓力而於 2020 年終止,成都領事館被關閉,使得他原有的身份與敘事位置變得更加脆弱。
無所逃離的政治,一場漫長的告別

如果說《江城》源於好奇,《別江》則是一本告別之書——告別一座被水位與制度共同改寫的城市,告別一個相信未來會逐漸開放的年代。
舊城沉入水底,舊時代沉入沉默,留下的是一個更整齊、更現代,但管制更嚴格的社會。
從《江城》到《別江》,何偉示範了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承認複雜,容納矛盾,拒絕把世界壓縮成可供快速消費的結論。
他在採訪中說,「中國寫作(China writing)正在變得更狹窄,它變得更政治化、更注重安全。人們正在失去那些人性層面的元素,而我真心希望這種狀況能有所改變。」
但當然,他並非迴避政治,事實上,不論書中他寫身邊的人,或者他自身的遭遇,處處都可以看見政治的的烙印如何影響人們。包括他的言論在網路上被舉報,有美國外交官提醒他可能被逮捕。全書故事的最後是他無法留下續約教書——很顯然,這是被政治決定的。
書中最後一章寫到,「一切都改變了,但一切也都沒變。」何偉在媒體採訪進一步詮釋這句話,「掌權的仍然是同樣的政黨,同樣的政治體系,而且在許多層面上,在2019年比我離開時的1998年限制更多。這是最令人好奇的:為何當社會一切層面都改變,卻沒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改變?」
長江仍在流動,但河岸旁的人事物卻不斷變換。在所有可見的變化之下,始終有一條從未消失的河流——政治權力。或許,這才是何偉書寫的中國日常中,那條真正影響一切的「另一條河(別江)」。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