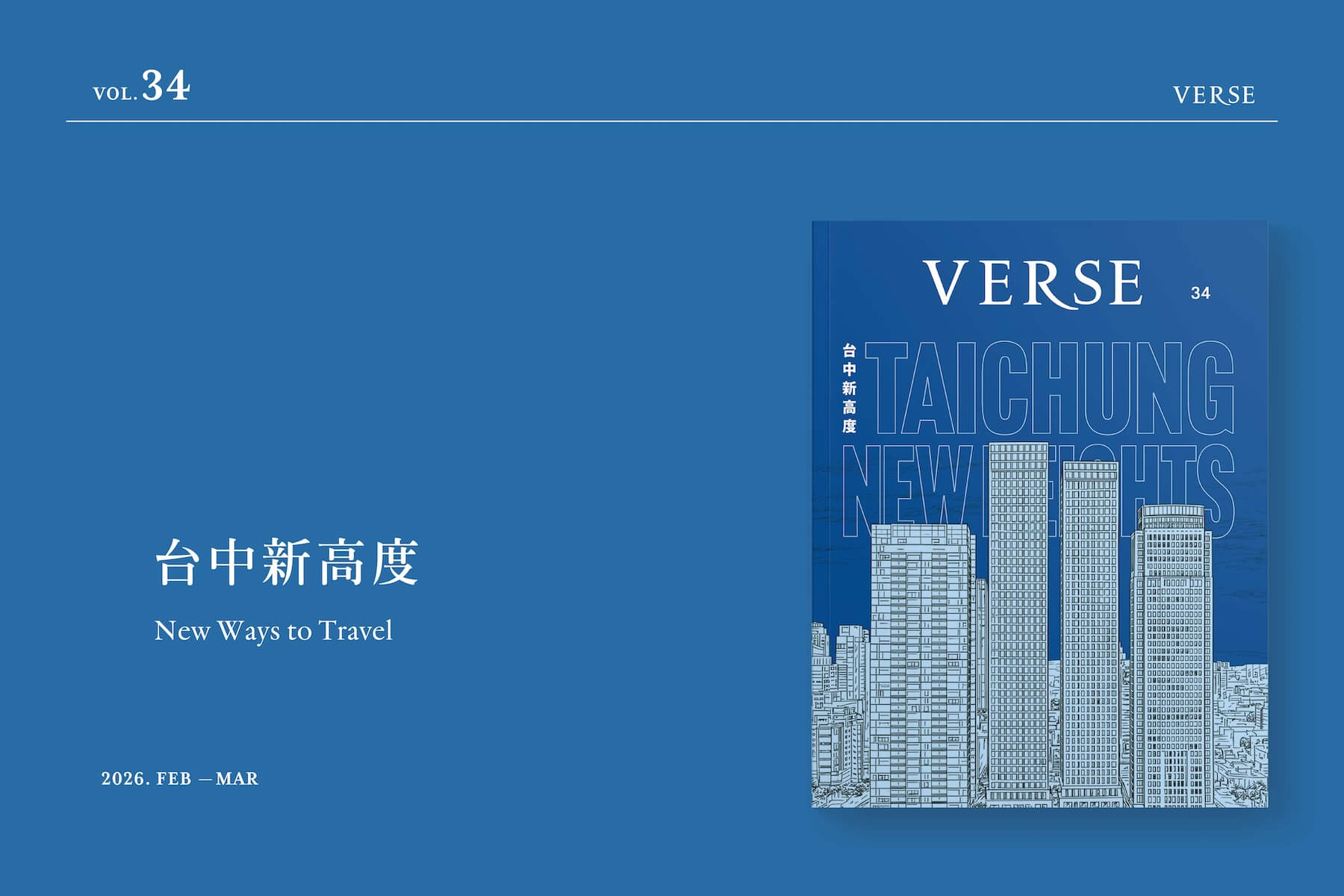王榮文與遠流的50年文化編年:一位出版人與他的時代長談
自1975年創立以來,遠流不僅是台灣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更是台灣文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從三毛到金庸,再到90年代的台灣館、傳播館等叢書系列,遠流的出版反映了時代的集體心靈,引領新的社會思潮,培育許許多多作家,更改變無數個心靈。創辦人王榮文五十年來始終在出版線上,也是極少數見證50年台灣出版史的重量級前輩。這篇萬字訪談不僅回顧了台灣出版史的重要篇章,更讓我們深刻理解出版的歷史就是一部思想的歷史。
PROFILE |王榮文
1949年生,嘉義人,自小鍾情閱讀,學生時期便展現對文字與出版的敏銳度,曾擔任南二中青年社編輯,進入政大後成為《杏壇》總編輯。1975年創辦遠流出版社,以實驗精神與文化理想為基礎,投入辭典、學術、文學、小說、旅遊、圖像書、兒童繪本等多元出版領域,攜手三毛、李敖、柏楊、金庸等人開創文壇創作歷程。早年出版代表作包括《拒絕聯考的小子》、《心理與人生》、《情感與人生》、《遠流活用英漢辭典》、《中國歷史演義全集》等,確立多角化經營路線。
他是最早投入電子書、知識庫與數位平台的出版人之一,也將出版理念延伸至空間實踐,參與華山文創園區轉型,推動台灣設計、藝術與文化對話。50年來,他持續提問、創新,將出版視為不段延伸的文化實踐。
 遠流出版社 創辦人 王榮文
遠流出版社 創辦人 王榮文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遠流今年正式成立50週年,代表王董見證台灣出版業50年的變化,從戒嚴時期到現在的數位時代,讓我們從基本問題開始。首先想問您的是,童年時期是怎麼培養出閱讀的樂趣?
王榮文(以下簡稱王):如果要用關鍵字來形容我啟蒙階段的閱讀經驗,那大概就是「五角無限本」 。當時鄉下的租書店是這樣的,進到書店時付五毛錢就可以看各式各樣的刊物,我當時常常拿著五毛錢去租書店看遍那裡的漫畫、小說,還有《中央日報》的副刊等等。到了初中,我到嘉義念書,那時候開始有剪報的習慣,報紙上看到好句子,我會剪下來貼在筆記本,後來到初中末、高一時,我又受到胡適影響。胡適不是寫日記嗎?我就模仿他,開始寫所謂的「胡適體」日記,用條列式紀錄每天發生的三件事;後來在高二那年,我成為南二中青年社的社刊編輯,接著到政大唸書,當了《杏壇》的總編輯。
鐵:所以您對出版的興趣幾乎可以說是從高中就開始?
王:是啊,進政大以後,我因為分數差一點點,進了教育系而不是一開始想讀的新聞系。雖然當時對教育系有點不滿,但我還是希望在系裡找到認同。那時候我很欣賞的教授是呂俊甫,他講過一句話影響我很深:「讀教育就是要影響別人。」
編輯《杏壇》時,我從畢業校友的通訊錄裡看到吳靜吉寫的文章,那時候他剛讀完心理學博士學位,字裡行間都是充滿文字的魅力,我很認真地寫信約稿,因此認識他,就一直到現在。後來我又去應徵《海外學人月刊》編輯,當時總編輯是創辦過《大學雜誌》的鄧維楨。他特別欣賞我,什麼稿子都叫我寫。
後來去當兵,快退伍前鄧維楨寫信給我說,「你不是說要做出版嗎?那我們來做吧。」
鐵:他當時為什麼是找您一起創辦?
王:當時鄧維楨對我説,雜誌我們要辦得像Time、Newsweek那樣有影響力,如果我們在雜誌上號召全台灣人穿短褲,大家就真的會跟著穿短褲。
現在回頭看我才會想,奇怪,他為什麼不是找我去當員工,而是說「我們一起創業」?他還對我說:「你沒錢沒關係,去借。」我就真的跟媽媽借了四萬塊,還到處去募資。我們當時設定的資本額是一百萬,他、他弟弟跟我三人分頭去找資金,有幾十個小股東,最後我湊到的錢還比他多,總共募到六十幾萬。
鐵:您那時候的職務是什麼?
王:他一開始就給我《太平洋雜誌》發行人的頭銜,還真的印在雜誌上,他是真正的老闆,也是總編輯。
第一期銷售不理想,而且第二期還沒出來,警總就知道我們的內容,就封掉了。後來鄧維楨跟我用剩餘的資金和沈登恩合伙成立遠景出版社。遠景在1974年剛創辦的那半年是我一生裡最精彩的時光。我們兩個月出四本書,白天我是出版社老闆,晚上我是吳靜吉的研究助理,沈登恩騎著摩托車,載我去做發行印刷廠,在那半年教我從最基層的包書,發行、收帳,鄧維楨教我編輯。
鐵:遠流的成立,聽說是因為吳祥輝的書《拒絕聯考的小子》鬧翻了?
王:真的不誇張。鄧維楨是遠景的總編輯,他看中吳祥輝的稿,但身為總經理的沈登恩反對出吳祥輝的書。我後來常常描述我們這個二比ㄧ的情況,如果是民主時代要投票的話,我是那位舉足輕重的決策者,我看他們誰說得有道理就投給誰,所以他們兩個都對我很好。
那時候恰好是我們創業快一年,公司賺錢賺了18萬,於是吵架後,鄧維楨就跟沈登恩建議我們拿出一些公司賺來的錢成立一間新出版社來讓我來經營,這樣我們有兩間出版社,可以解決一些困境。沈登恩不小心講了一句話,說我什麼經驗都沒有,所以就不願意一起成立新公司。他講的也是事實,不過後來吳靜吉跟鄧維楨都投資十萬,還有薇薇夫人也投資,就開了遠流出版社。
後來鄧維楨又看上一本書,吳宏一主編的關於古典詩詞的《江南江北》,沈登恩又否決掉那個書。鄧維楨就又找到他的學弟劉君業來合夥開一家出版社「長橋」。一本被拒絕的書就產生一個新出版社。那個書之所以賺到錢,跟鄧維楨現在的太太黃寶雲很有關係,因為黃寶雲在教育部上班, 可以拿到全國的國文老師名單。
鐵:您是在1970年代初進入出版業,在那之前的台灣出版環境大致是什麼樣貌?我看到有些書稱您是「戰後第一代出版家」,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說法?
王:這個「戰後第一代出版家」的說法,是詹宏志寫在某本雜誌上的形容。如果要談台灣的出版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是日本時代的漢文出版,像嘉義的「蘭記書局」與台南的「興文齋書局」,雖然是書店,其實也兼具印刷出版功能,蘭記書局在日本時代主要做漢字書出版,其中少數像是字典、台灣話教材是自己編輯的,大部分仍然是進口書。
第二段就是1949年之後,重慶南路那一帶興起的出版社,包含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中華書局、東方出版社等。他們大多以重印大陸書籍為主。即便像《籃球情人夢》或金杏枝當時暢銷的大眾小說,其實都先在大陸出過,後來為了怕麻煩就會改名字重新出版。
我們這一代被稱為「戰後第一代」,因為我們出生於1949年,受完整的國民黨教育,到大學畢業是1970年代初。1974年時我們創立遠景出版社,那時已經是台灣人開始自己開出版社的時代,像藝術圖書公司、三民書局、文星書局等等。
鐵:讓您感受到文化震撼、打開視野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王:我真正的啟蒙,理論上應該是《自由中國》、《文星》雜誌。雖然我後來也出版過雷震的書、與雷震的女兒有些往來,但事實上打開我視野的是《文星》。
1967年我從南部上台北來念大學,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來台北。我第一次受到文化震撼,是來自峨眉街的文星書店。68年文星書店在做清倉拍賣、準備收攤,櫥窗內有龍思良的設計,把書跟雞蛋擺在一起,海報上寫著「播種者胡適」。我一個鄉下小孩看到那樣的畫面,整個被衝擊到,「哇,原來書店可以這樣搞。」
(編註:隱地先生描述那個場景:「書的旁邊,還有一籃雞蛋,雞蛋邊上,放著一張照片和一行題字——播種者胡適寫的「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
那時我們學生買書都去師大的長榮書局,書店老闆張清吉後來創辦了志文出版社,出版了影響力很大的《新潮文庫》。因為牯嶺街、師大那一帶的書最便宜。文星書店的叢書作者,包括李敖、陳之藩等人,原本對我來說都是書上的名字,沒想到我做遠景的時候,他們一個一個變成我有機會接觸的大作家。這些人有很多都是沈登恩介紹的。
我們那個年代的作家、藝術創作者都很期待有知音的出現,有人真的看得懂他寫的東西、喜歡他,即使出書不賺錢,那種支持對創作者來說很重要。
當然,李敖就不是這種人。沈登恩第一次帶我去見他的時候,李敖還拿出沈登恩高中時代寫給他的信。誰會知道沈登恩未來會變成遠景的老闆?但李敖把那些信都留著。他是一個對資料極度執著的人。我第一次去見他時,他已經把我以前在報紙上被訪問過的內容都看過、整理好,且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這就是李敖。

鐵:您曾說自己是從文星書店啟蒙,甚至買下它的圖書館,某種程度上像是延續一種出版精神?
王:做遠流第二年,我就花十萬元買下蕭孟能在安和路文星書店的圖書館。那對我來說是夢想成真,因為我的啟蒙來自文星書店,能接手他們的圖書館就像是買下一種傳承。還記得當時我用七輛卡車搬書,李敖的家就住在那間圖書館的對面,他當時看我在搬書還笑我說:「你這個大笨蛋,花十萬塊買一堆垃圾幹嘛?」他說他早就已經把所有好東西都搬回家,留給我一堆沒用的書。
蕭孟能有一本書《出版原野的開拓》,講他作為出版人的夢想,那是影響我很深的一本書。我其實某種程度上覺得我延續了這個精神,繼承了文星的出版理想,當時李敖笑我我也不以為意。
鐵:遠流創立初期,前幾年的出版品是什麼方向?
王:我常說我是這個圈子裡唯一一個沒有專長的人。別人做出版,大多有強烈的偏好和專業,比如沈登恩熱愛文學、藝術圖書公司專注藝術、戶外生活圖書專精於戶外,我是樣樣有興趣,但樣樣不精。
所以我做出版初期,撿到什麼就做什麼,碰到誰就做誰的書。「因緣際會」這四個字很適合運用在我的人生際遇中。生活中,我的貴人不斷出現,不是我能幹,而是時機剛好、人剛好出現。你問我對什麼有特別有興趣,我那時候對字典、百科全書就有一些興趣,大概是因為自己不太會讀書,所以對這類工具書特別有感。當時做出版的人最喜歡去日本,特別是海盜時代我們沒有版權的觀念,我到日本書店看到哪一本最暢銷就出那一本,所以當時在日本看到《活用英單一萬字》,遠流就把它變成《遠流活用英漢字典》,吳靜吉博士策畫,非常暢銷。
後來我拿到三毛的地址,就寫信給她,但是她所有寫的任何一本書,都必須給皇冠出版。我沒有放棄。我說有沒有別的可能性?她就說,我現在每天在炒菜,在廚房做菜的時候,我就看一下阿根廷漫畫家季諾的漫畫,笑一下再去炒菜。你們有出漫畫嗎?如果我來翻譯這個漫畫,應該不算我的創作。我說遠流沒有出漫畫,不過如果你要翻譯這個,這個蠻好的。這就是《娃娃看天下:瑪法達的世界》。三毛當時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介紹,結果賣了五千套,賣得非常好。這讓我了解在三大報壟斷媒體的年代,明星的影響力比廣告還強。
跟李敖合作《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時,我知道明星的力量,堅持這套書一定要由李敖主編,李敖原本跟我要25萬,但他說如果你要掛名李敖策劃、主編,要再加60萬,一下變成85萬。我那時又開始計算成本、印量、廣告等等。我們也想好slogan「以書櫃代替酒櫃。」在那個時代氛圍裡,那是很有意義的句子,因為當時大家賺到錢就是買房子,買了房子之後家裡則是放酒,但我們提出倡議要大家不要放酒,改放書。
鐵:一開始怎麼會出版李敖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王:李敖那時候剛出獄很窮,他拿《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問沈登恩出版。其實那書不是他寫的,主要內容也是大陸的書《歷代通俗演義》,他改了名字,每篇前面加上五百字導論,當然這就是企劃能力,他要賣25萬。沈登恩說他不買,幫他介紹康寧祥跟司馬文武,因為康寧祥要選舉,李敖就對他說:「你不是很多人要捐款給你嗎?你不如印一套《中國歷史演義全集》賣書可以募款。」司馬文武跟康寧祥想了很久,最後還是放棄。我是他的第三個選擇,那時候我還不認識李敖,但是對出版這套書有興趣。實際上我腦袋有一個計算的基礎,因為我那時候剛從《活用英漢字典》賺到了兩百萬,買了一棟房子,我想如果這套書最後賣不出去,大不了就賠掉這棟房子,於是我決定接下來做這套書。
鐵:進入80年代,一切時代氣氛應該都不同了。
王:那時候我們做出版,表面上《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帶來很可觀的收入,但說實話,我不會理財,我不像鄧維楨的太太那樣會打理財務,錢雖然賺進來了但也很多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花出去。
賺錢之後有很多不快樂。有功勞的人太多了,從李敖到我們內部的員工,每個人都有份,所以錢一進來,問題也跟著來。隨後我們又碰上出版接連不順。李敖後來也把《中國名著精華全集》賣給我,但出這套書讓我徹底看清楚一件事:廣告的魅力沒了。
1980年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1982年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那一年也出版《中國傳統音樂》,這套書是從日本來的,那時候日本正在整理中國傳統音樂,對中國地方戲曲、京劇的研究很有系統,也正逢一波中國熱,所以跟那一圈學者有了往來。像我今天還能跟邱坤良保持這麼深的交情,其實也都是從那個案子來的。他當時不懂日文,但我們翻譯完之後還要做校定,要補中國傳統地方戲,要調整文字系統,因為日本人整理的內容跟我們的語感不太一樣,很多東西都要重寫。那整個系列,其實是我賠得最慘的一次,連廣告都沒人看。
鐵:那時候的出版環境是什麼樣?
王:那時候我們想做創新,做了多媒體版本,包含有文字、CD的刊物,結果市場根本不接受。我們嘗試了很多,也賠了很多錢。賠錢當然就要借錢。其實那時候的出版界資本都很少,我們這些戰後第一代的出版人,創業的時候大概只有30萬資本,有的還是借來的,出完書之後,可能開給印刷廠的是三個月期票,書店回收是四個月,這中間就要一個月的周轉金。作家的稿費先付、編輯的薪水先發,所以即便是暢銷書也會有周轉的問題。
那時候還有票據法,所以整個出版圈幾乎都在跑三點半。我運氣比較好,差不多每段時間內都有暢銷書,比較少跑三點半,但偶爾還是會缺錢。那時候利息很高,兩分一已經是最便宜的,普遍是兩分四,甚至三分利,一年下來三十幾個百分比,現在銀行不過四趴、六趴而已。這就是為什麼那一波會倒這麼多出版社。
沈登恩就是在那個時候借不到正常利息的錢就借到地下錢莊。不過,在遠景還是很神氣的時候,1978年4月,鄧維楨發現沈登恩的驕傲之心已起,就邀我與他拆夥了。
我當時認識一些紡織界的朋友,他們發現借錢給出版人助人利己。我還當過「牽線人」,幫出版社找資金。初期有時候我們還要作保,但後來就不敢擔保了,因為有些出版社,借了錢就是還不出來。陳宏正先生那時候也借過我們錢,他當時幫了很多的黨外作家,被稱為「文化遊俠」。
1986年出《胡適作品集》也是由陳宏正牽線。他知道我崇拜胡適,也知道胡適紀念館需要經費,於是介紹我認識胡適紀念館的館長王志維,由詹宏志擔任總編輯,出版《胡適作品集》。那時候都在出大套書,《胡適作品集》出了37本,對出版社來說,意義非凡。
後來我們又出《胡適日記影印本》,因為胡適紀念館沒有錢維修房子,所以我就答應用一百萬買了胡適日記的版權,那在當時來說是很氣派的。不過,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胡適的兒子胡祖望擔心他爸爸寫的日記得罪人所以不願意,也因此這件事情來來回回溝通了很久,最後他終於同意。最後大概賣了一千套。一百萬有沒有回本,我不知道,但這是夢想與勇氣。
在出《胡適作品集》之前,我們在1983年先出了《柏楊版資治通鑑》的第一冊《戰國時代》,其後每月出版一冊。那段時間我其實剛經歷《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失利,發現用套書的形式在市場上已經賣不動了。詹宏志提出叢書雜誌化,於是《柏楊版資治通鑑》就像雜誌一樣一個月出一本。
接著詹宏志跟我就進入遠流的開疆闢土時代。從《大眾心理學》全集開始,他進來當遠流的總經理,然後找周浩正來當總編輯,還有陳雨航等一個一個都進到遠流,每個人都開拓一條線。這個時候我也引進金庸。
大眾心理學的書種子來自鄧維楨,他當時財務困難,所以賣給我40本心理學書的翻譯權,加上我自己出過十幾本心理學的書,有50、60本了。所以詹宏志就說好,我們就開一個大眾心理學全集。化整為零系列書的時代開始了。
鐵:後來台灣館系列叢書影響深遠,據說也採取了很特殊的工作模式。
王:當時《漢聲》來到遠流的人分成兩組,莊展鵬帶人做台灣館,郝廣才帶人做兒童館,在遠流的那段全盛時期,他某種程度上就是從選最難做的繪本開始,一步步開拓國際市場,像是帶著遠流的童書到波隆那。台灣館的第二任總編輯也是從《漢聲》出來的,包括傅月庵,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台灣館的編輯,記得他還跟我說過「在出版社工作這麼好?每天讀書還發薪水。」那個時候,台灣館有11個人。
台灣館的成立是出版史上絕無僅有的,某種程度上,他們從《漢聲》學到一些工作方法,開始有意識地要整理台灣,這11個人每天都在讀書,每天開會就在讀台灣歷史,甚至收集相關的幻燈片,現在遠流汀州路最珍貴的藏書跟幻燈片,很多就是從台灣館留下的。
因為台灣歷史那時候還沒有太多人懂,他們必須找教授來講課,所以找了吳密察在遠流汀州路的辦公室總共講了兩年的書,那兩年的學習、思辨與積累,對那一整代編輯來說,是一種奠基。
鐵:11個編輯,讓他們兩年只出一本書,真的是太特別了。
王:這正是為什麼我在談台灣出版史時,會特別提到,如果有人對台灣出版有貢獻,那金庸也該算一份。因為說實在的,我從出金庸的書賺了很多錢,但我沒有拿那些錢去蓋房子,而是選擇繼續留在出版業,用賺來的錢投資出書,尤其是像台灣館這樣讓他們兩年來都在讀書。他們慢工出細活,所以後來做了一系列觀察入門的系列。從台灣館那個體系下來就可以說很多故事。
不過有點可惜的是,因為我們最早成立台灣館,投資也最大,但因為他們的工作方法跟堅持,所以我們出書量不如後來的遠足,他們懂得運用大學教授指導的台灣歷史、地理資料,以圖文並茂的方式編寫成大量的台灣歷史地理百科,路數不同,各顯神通。
鐵:所以您們是真的把賺來的錢,拿去做那些不一定暢銷、但很有價值的學術書?
王:這就要說到雄才大略的詹宏志。其實那一段時間,大部分重要的出版幾乎都是由他來找人與規劃。我對他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他想做什麼我就全力支持。詹宏志讀的書多、腦袋好,而且沒有一個編輯又會做生意,又會讀書,所以雖然過去我跟沈登恩、鄧維楨學過一些東西,但等到詹宏志出現,我都是聽他的。我真的太依賴他、太喜歡他了(笑),只要他接手,我就很放心。
鐵:您為李登輝總統出書這件事也很有歷史意義,這是第一次民間出版社為在任總統出書,當時什麼淵源?
王:這是一個觀念。我之前出了陳舜臣的書。他是新莊人,三歲時去了日本,成為日本重要的歷史小說家,每次他回台,李登輝都會邀他吃飯。我心裡想,有一次我就跟鄭淑敏說,請他跟蘇志誠建議李登輝,下一次陳舜臣回來時,不要只是在家裡吃飯,應該用總統的身分正式接見他,彰顯總統對文化的重視。
結果他聽進去了。於是陳舜臣夫婦回來時,在蘇志誠安排下,我陪同他們進了總統府,那是1994年。那是我第一次踏進總統府,特別對一個從鄉下來的孩子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作為一位出版人,我腦袋裡想,每個人都欠我一本書(笑),既然我要進總統府,我就想要約稿,所以那一天他們聊天時,我找到機會提議為總統出書,當時總統也很豪爽的答應。不過後來總統透過蘇志誠傳話表示《經國先生談話筆記》這本書還不太適合出。於是我就問:「那怎麼辦?他答應了,有沒有其他可能?」
後來我們討論出一個方案,就是整理他過去當市長、副總統時的演講稿編成一本書,正好當時我還在政大企家班念書,腦子裡一直想著經營,所以《經營大台灣》的書名是這樣來的。
鐵:所以這本書的名字是您取的?
王:對,我就地取材,然後找李仁芳做編輯。我把所有的文章整理好後給李仁芳,問他書怎麼編比較好?在討論過後決定分「經營市政」、「經營省政」、「經營國政副總部」,還做一個附錄「經營家政」,就是他懷念他兒子李憲文的文章。我還請董陽孜來寫書法題字。
我認為出版人的責任不只是完成出版,還要找到好的編輯、作者,出版後更要做行銷。當時我也不知道這書能不能賣,理論上應該不容易賣得動,但畢竟是總統的書,意義非凡。也因此我提出建議,既然是總統的書,我必須付稿費、付版稅,不能太少。後來我還跟蘇志誠商量,說我要付一百萬版稅!總統不拿版稅,但我說不行,這錢是我該給的,於是我們後來決定把版稅以他的名義專捐出去。
那時候全台最好感的人就是李遠哲,因此我們決定把這筆版稅捐給他經營的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這是出版人在行銷上創造價值的方式,因為只有做有價值的事,才會產生真正的價值。我們在國家圖書館辦了一場公開捐贈儀式,當作新書發表會,這應該是1995年左右。
有趣的是,李遠哲的基金會當時已經募到他們的目標款項,於是跟我商量,希望把50萬分給他一個好朋友的基金會,這位朋友也是化學家。於是我們就把50萬給了李遠哲,另外50萬捐給張昭鼎基金會。
鐵:您怎麼看待編輯在創作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又該怎麼拿捏介入的分寸?
王:創作本身就是一件艱難的事,身為編輯,重要的是怎麼協助作者度過那些難關。當然,有些作品是作者早已寫好的、成熟的內容,這種直接出版也沒問題,但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作為另一種類型的編輯,或許就有機會成為創作者過程中的助力,幫助他穿越瓶頸,走出低潮。
像我身邊的同事正在幫我寫回憶錄,現在正陷入創作難關。我甚至跟他說:「你可以把這本回憶錄當成小說寫。」因為他一開始的心理障礙是王榮文是老闆,好像不能亂寫。但其實這是可以克服的。
他是學華文創作的,像他這樣受過創作訓練的人,不但不想重複別人,也不想重複自己,即使是書寫同一個人物,他還是想寫出新的東西。像李安、金庸這些創作者,他們都是如此。但是對每一本書、每一段文字來說,到底哪一部分做到創新,只有創作者自己明白,所以更需要讀大量素材去找切入點。這半年,我等於是一路看著他訪談、閱讀、整理素材,我們之間也互動頻繁,有些話是我想講給他聽的,有些則是他想挖掘的。他不要那種已經被別人訪問過、講過、寫過的東西。結果你知道他最後怎麼突破嗎?有一天我把我從初中、高中寫的日記、筆記通通拿出來給他,該看的、不該看的全都攤出來,這下他好像找到了和別人不一樣的切入方式。
他也用心地讀我那些日記,然後用裡面的句子來回應我現在的說法。從這個方法來看,他其實是在閱讀不同年齡階段的王榮文,從18歲、38歲、58歲、78歲,然後比對這些不同時期的我。現在他好像真的找到那個切入點,章節也都架構出來了,只是還沒交稿(笑),我也不敢催稿。
這就是我看到的整個創作過程:從訪談、文本、日記、閱讀,寫作時他需要了解那個時代,所以他也得讀那些影響我一輩子的書、人和事情。這段經歷也讓我思考,如果我是編輯,面對這樣一位作者,我該怎麼陪伴他、鼓勵他,讓作品完成。
鐵:大家都知道進入21世紀以後,數位化對出版產業影響很大。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感受到這種挑戰?有沒有哪個關鍵時刻,讓您覺得出版產業過了輝煌時代?
王:我大概是在1996年左右出版了比爾蓋茲的《擁抱未來》(英文名:The Road Ahead)。如果我沒記錯,這是台灣出版史上第一次預付版稅超過13萬甚至15萬美元的案例,當時其他書的版權通常才幾千美元,但為了搶到這本書的中譯版,我們出手相當大方。
那是網際網路剛剛開始興起的年代,我在溫哥華學習了不少關於Internet的知識,接著也開始做金庸茶館、博識網,推出電子書、CD-ROM產品。2000年左右,遠流的電子書工作室成立,我也投入大量資金和資源、投入智慧藏的學習科技研發。當時對我來說,這是出版的新時代,我充滿期待,覺得透過網路讓字典、百科全書等內容可以隨時更新和刪除,非常便利,後來我們更嘗試做金庸閱讀器,並且在硬體設備上跟鴻海的孫公司有合作計劃。可惜的是,因為我不熟硬體軟體,整個項目最終是失敗的。
現在歷史再給我第二次機會,AI來了(笑)。從上次我學到了什麼經驗?我不會花力氣在自己不熟悉的硬體上,而是要聚焦AI如何改變出版,例如ChatGPT在出版的應用。過去那些主題知識的智慧藏,集天下書於一書的概念,其實都有可能成為未來的主流。
比如說,我掌握了金庸博物館完整的資料,裡面有些是有版權保護的,有些是公共財產,如果把這些資料餵給主題型AI,讓它理解並回答問題,那將是什麼樣的商業模式,目前還很難說,但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會看到AI在出版上的應用,這讓我感到非常興奮。
鐵:那傳統出版業面對這樣的挑戰會不會特別艱難,尤其像你們那麼大的出版社?
王:不見得是因為規模大而特別艱難,因為出版行業裡很多創作都是非常私密、很個人,畫畫是這樣,寫作也是一樣。對於出版,我認為有一些本質是永遠不會變,就是人類本質上想要表達自己要創造一種新奇的東西,想要追求不同,想要超越別人。
作為編輯,不管是用文字、紙本,還是數位平台,這都歸類為出版品。從我年輕開始就自認為是一個出版人,哪怕現在我在經營華山,我也把它當作一個空間媒體來經營,只不過這裡用的不完全是文字,可能是身體、藝術或其他形式的表達。換句話說,在數位時代,包含AI這些新技術,都屬於出版的範疇。從我的視角來看,出版從來不是僅限於某一種形式。
再舉一個例子,我算是很早開始做電子書,因為當時我被比爾蓋茲的預言誤導。他預言到2020年,美國98%的出版會是電子書,只有2%是紙本,而我們現在來到2025年了,美國也沒發生這種情況,電子書並沒有取代紙本。後來我讀了《追蹤哥白尼:一部徹底改變歷史但沒人讀過的書》,從這本書我理解到人類的閱讀習慣,以及印刷、出版習慣,我理解到這些習慣要真正被取代沒有那麼容易,所以現在我回頭認真做紙本出版,與此同時還是很認真關注電子書的發展。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