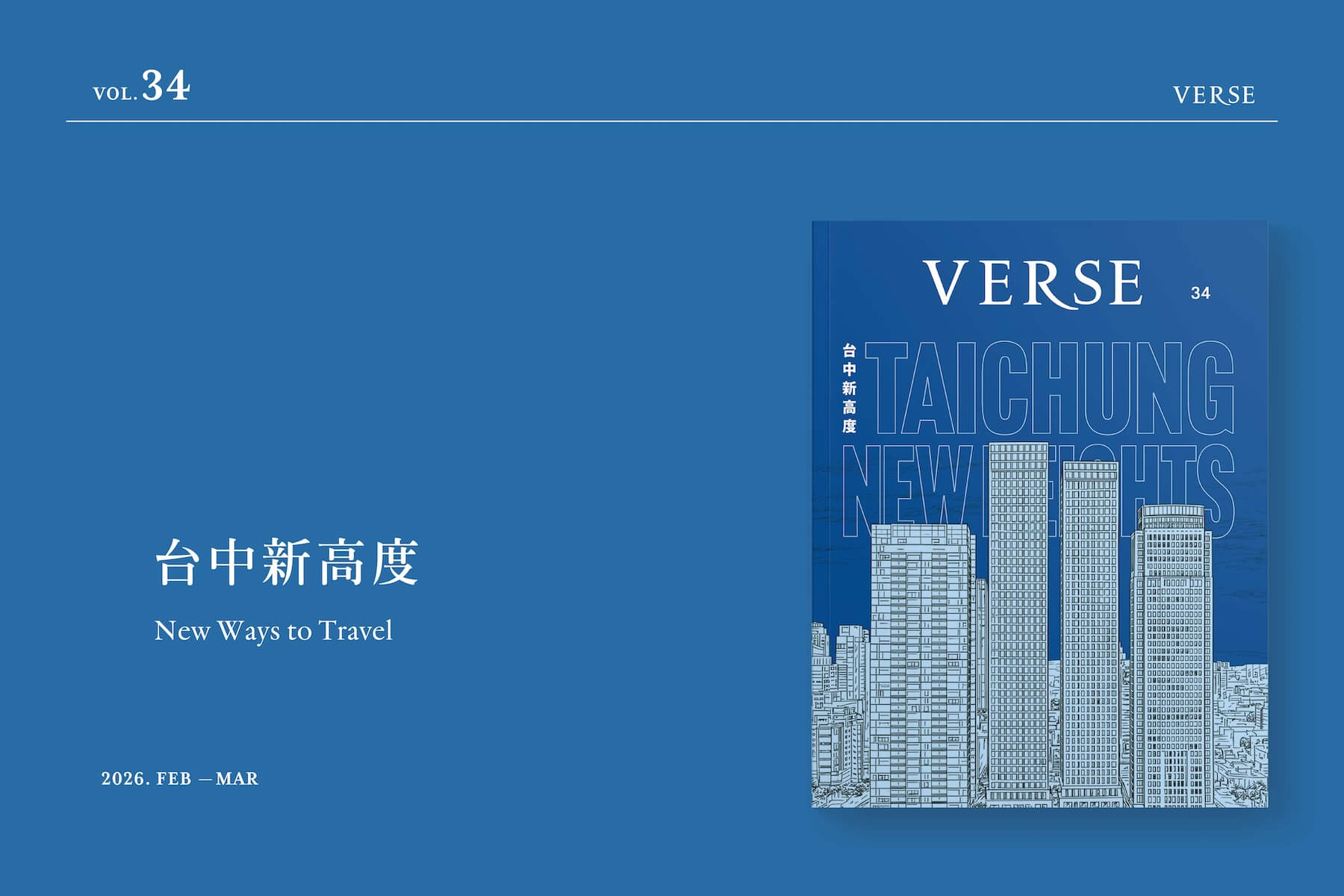早餐店番茄醬的秘密:日俄戰爭如何成就「臺南可果美」?百年醬料背後的帝國史
《此地即世界》是一部從台灣出發的全球史,透過20個台灣在地地景,從小琉球的烏鬼洞、屏東的鵝鑾鼻燈塔,到臺北的明星咖啡館、永和中興街的小吃攤,揭示我們身處的島嶼如何與世界交織,證明台灣本身就是世界歷史的現場。〈臺南可果美〉這篇文章深入探討番茄醬和番茄罐頭的百年歷史,揭示這項日常美食如何從日本明治維新、日俄戰爭,到在台南生根,成為你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傳統早餐店裡的薯餅和小熱狗,要擠上番茄醬才對味;而茄汁鯖魚罐頭,更是另一項加上番茄醬汁就讓食物風味翻轉的例子。儘管不少人拒生番茄於千里之外,但透過一道道神奇的加工手序,番茄製品早已成為臺灣人日常吃食中不可或缺的一味。
番茄製品如何攻佔台灣人味蕾?

它的「番」字,似乎和「番麥」、 「番石榴」及「番薯」一樣,暗示了番茄是由外國人引進;而我們確實也總在義大利麵、薯條和熱狗這些歐美餐飲中,嚐到番茄的鮮味。不過,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臺灣人認為最本土、坐擁最多臺灣傳統美味的臺南,卻有一家專門生產番茄醬、番茄罐頭這些洋派番茄製品的「可果美」公司——而且,深究可果美的背景,更會發現它並非來自番茄醬大國美國,而是與擁有番茄般紅通通太陽國旗的日本有所關聯。
西洋的番茄、日本的可果美,怎麼會匯聚在臺灣這座島嶼上?
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把目光轉向鄰居:東洋日本。因為,臺灣番茄製品的起飛,正與日本海軍的戰艦有深刻的淵源……
新時代的舌頭,新時代的蔬果:明治維新的洋食料理

在日本,與番茄醬搭配的美味,正是隨著「明治維新」的演進而誕生。
十九世紀,日本有識之士從歐美各國的進逼中,嗅到山雨欲來的新時代氣息。他們所建立的新政府,有意識地移植西洋現代化的軍隊、交通設施和法律制度,使日本能夠穩定步上脫亞入歐的軌道。
不只是政策制度煥然一新,橫濱港邊的紅磚洋樓,街上著西裝、拄拐杖的男士,以及馬車、路燈和地下水的出現,都顯示出日本舉國上下的變革——甚至於,常民餐桌上的菜色也隨之翻新。
日本有近千年的時間受到來自中國的佛教戒律影響,多數日本人的日常吃食以不殺生、無肉為原則。直到明治維新時,日本自西方學習營養知識,希望國民養成如洋人般強健的體魄,紛紛提倡洋食和肉食。番茄,也趁著這波推崇洋食的風氣,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
其實透過早期的越洋貿易,番茄早已登陸日本。但是在缺乏相關經驗和品種改良技術的情況下,看著這顆又綠又紅的蔬果,散發鮮豔得詭異的顏色,日本起初只把番茄充作觀賞用植物對待。
直到洋食普及後,一八九九年,一位剛從日清戰爭服完兵役的日本人蟹江一太郎,回到老家愛知縣開始嘗試種植我們今日熟悉的大紅番茄。起初,蟹江將自己種的番茄賣給飯店與洋食店,但日本國民普遍對於鮮紅的番茄反應平平,不敢貿然食用。為了促進番茄的銷售,蟹江自己師法國外大廠,試著將其加工成各式製品,讓國民更能踏入番茄的懷抱。就這樣在一九○三年,蟹江研發了近似肉醬的番茄醬汁(Tomato sauce);緊接著,五年內,蟹江更做出日本第一罐番茄醬(Ketchup)。
 可果美創辦人蟹江一太郎。
可果美創辦人蟹江一太郎。
就像我們身邊有許多不敢吃番茄,卻喜歡吃番茄醬、番茄肉醬的朋友一般,蟹江的產品成功吸引日本人的注意。當時,可樂餅、漢堡排等洋食料理開始上了餐廳、乃至於日本國民們的餐桌,正好給了番茄醬大展身手,當一個最佳佐料的好機會。
而這位研發日本第一批番茄製品,讓番茄搭著洋食熱潮普及全日本的蟹江一太郎,就在一九一七年創立了日本最大的番茄製廠——也就是日後紮根臺南的「可果美」公司。
打贏了仗,就需要更多番茄:茄汁罐頭隆重問世
 番茄罐頭發明於19世紀初。
番茄罐頭發明於19世紀初。
說起日本對外戰爭,大家都瞭解影響臺灣歷史進程的日清戰爭,以及課本會提及、但我們不大熟悉的日俄戰爭。日本投入這兩場近代重要的對外戰役時,不只是軍隊、槍砲和船艦使用當時新穎的現代化裝備,士兵們食用的口糧,也進行了現代化的翻新。十九、 二十世紀之交,日本軍隊早就不像大河劇裡的士兵,吃著用布巾包裹的飯糰雜糧。魚罐頭、牛肉罐頭以及咖哩罐頭,早已見容於日本海軍的廚房內。
即食、品質穩定、種類豐富、保存時間又長,這些優點使得罐頭很適合當作軍糧。不僅如此,為了使巡航大海的士兵們不致迷失時間感,軍隊還會安排每週七天固定吃哪一種類的罐頭(例如週五固定吃咖哩)。
早先日本生產的罐頭幾乎都充作軍糧,而在日清戰爭到日俄戰爭十年間,產量更增加到九倍之多。罐頭的好,日本海軍都知道。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羅斯後,兩國簽訂了「日露漁業協約」(露指的是俄羅斯),保障日本漁民的漁網能撒向俄羅斯遠東,如千島群島、庫頁島周遭海域,甚至遠及堪察加半島處。這項條約使得大量漁產湧回日本本土,不只是漁民收入增加,更代表海軍軍人可以加菜了!
增加的漁獲,自然投入到易保存的罐頭製程中。但是,為了均衡充滿魚肉且時常口味過鹹的罐頭,罐頭廠們把腦筋動到了番茄上頭。富含維他命C,加上酸甜清爽的風味……這不正是罐頭所缺乏的嗎?
於是乎,番茄鯖魚、番茄沙丁魚、番茄鮪魚,這些我們現今在颱風天會屯購的番茄系列魚罐頭,於百年前隆重問世。只要是魚類,通通都能加入番茄一同醃漬,使番茄的需求量進一步大增,在二十世紀初期大舉受到日本國民的歡迎。需求量雖然大增,但萬能的番茄卻不是輕輕鬆鬆就能種出來。來自中南美洲的它,適合在溫度不高也不低的氣候種植。而每年冬季必定下雪的日本,除了溫暖的九州地區之外,只能在特定季節種植與採收番茄。
但是,別忘了,我們談的是一百年前的日本。除了北海道、本州、四國和九州,四季如春的臺灣,當時也是日本帝國的領地——腦筋轉得快的日本,開始將一顆顆番茄帶到臺灣島上,使臺灣歷史和番茄緊密交織在一起。
嘉南平原上竄出的鮮紅星點:臺南,成為番茄種植與加工重鎮
 「柑仔蜜」是南部人對番茄的獨特稱呼,這句話在嘉義、台南、高雄等地的水果攤特別常見,也常成為身處北部的同鄉人相認的暗號。(資訊來源:食農教育;圖片來源:無毒有偶)
「柑仔蜜」是南部人對番茄的獨特稱呼,這句話在嘉義、台南、高雄等地的水果攤特別常見,也常成為身處北部的同鄉人相認的暗號。(資訊來源:食農教育;圖片來源:無毒有偶)
其實臺灣與番茄的糾葛,和日本非常相像。
早在清國統治初期,番茄就可能經由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引入臺灣。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編修的《臺灣府志》上,就記載了現今臺語所稱的「柑仔蜜」(kam-á-bit),這很可能就是從菲律賓語kamatis演變而來。 只不過這時的番茄,是直徑不過一點五公分、味道清淡而充作觀賞用的小小番茄。就連十九世紀來臺的馬偕牧師也曾在日記裡頭提及,漢人和平埔族人都不甚喜歡這種味淡的小番茄。
直到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有了前文提到的洋食風潮與罐頭需求,在日俄戰爭後的一九○九年,才開始引入大番茄。隨後,臺灣總督府以臺南為中心,持續近二十年時間改良、擴大種植番茄。之所以選擇在臺南種番茄,一方面自然是拜嘉南平原的氣候所賜。臺南夏季炎熱,但冬季不易降雨又溫暖舒適的氣溫,完全是番茄最佳的生長環境。另一方面,秋、冬之際播種番茄,不會和甘蔗、稻米兩樣重要作物的時間有所衝突,使得農民們能夠將種番茄當作一筆額外的外快。
待到一九三○年代,番茄能夠穩定地栽種、採收,加工產業也應運而生。不過,設備、資本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番茄加工能夠順利展開,得力於早已足具規模的鳳梨罐頭產業。由於配合鳳梨的產季工作,鳳梨罐頭工廠原本在冬天並未運轉;直到番茄的大量種植,讓他們嗅到另一絲商機,不少加工廠才開始全年無休,輪番製作鳳梨及番茄製品。
隨著番茄製品產量增加,日本內地的大廠牌也注意到臺灣的番茄及番茄加工廠,甚至連可果美都派員調查來臺設廠的可行性。只可惜當時的可果美認為,臺灣工業用水不足,番茄表皮雜質洗得不乾淨,因而打消了設廠的念頭。
儘管如此,臺灣的番茄和加工業者卻相當爭氣,憑藉內需和外銷,將臺灣番茄送到家家戶戶的餐桌上頭。對內,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開啟和日本類似的現代化、西化進程,因此出現了一批喜好洋食口味的內需市場。對外,番茄加工廠利用臺灣秋冬產季的優勢,大量輸出番茄至日本、滿州,甚至在二戰時期跨洋外銷至歐美國家。
沒有大企業的加持,番茄農和工廠主們靠一己之力打拚,將這顆西洋蔬果,透過臺南的陽光、空氣和水,轉變成東洋人的口味,進而再次越過重洋,輸往世界各處
尾聲:可果美終究降臨!再探番茄的百年身世
 台灣可果美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67年,由台南食品工業、可果美株式會社、三井物產共同出資,主要生產蕃茄產品及其他食品加工銷售。
台灣可果美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67年,由台南食品工業、可果美株式會社、三井物產共同出資,主要生產蕃茄產品及其他食品加工銷售。
到了戰後,日本殖民統治結束、總督府撤離臺灣,而臺南的番茄田,依然在嘉南平原吸收充沛的陽光,緩緩生長。
但不知是歷史的巧合,抑或是命運的安排,一九三○年代放棄在臺灣設廠的日本大廠可果美,卻在三十年後的一九六七年與日本的三井物產、臺灣的臺南食品共同出資,並選在當初的番茄種植、加工重鎮——臺南,成立了「臺灣可果美」。
臺灣可果美正好承接一九五、 六○年代美援的結束,並準備迎接 一九八年代大型西式餐飲入駐臺灣。這兩個臺灣飲食史的座標,讓他們的番茄和番茄製品,走入家家戶戶的餐桌,也成為美而美、麥味登和呷尚飽早餐店的必備醬料。

儘管番茄早已滲入我們習慣的西式餐點裡頭,難以想像我們習慣的「番」茄與紅毛「番」關係不大,反而和日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有趣的是,關於這段隱微的歷史記憶,還能透過臺語尋覓到片面的線索:前面提到番茄的臺語是「柑仔蜜」,但或許生活中也時常聽到另個版本的說法——「偷媽偷」(トマト)。這個以一口日式發音唸出來的英文單字,又轉化成為番茄的另一種台語代稱。唸著這個打趣的名字,或許更容易讓我們想像,自日本時代起,一顆顆「偷媽偷」在嘉南平原上頭,受到農民細心培育、採摘、加工的百年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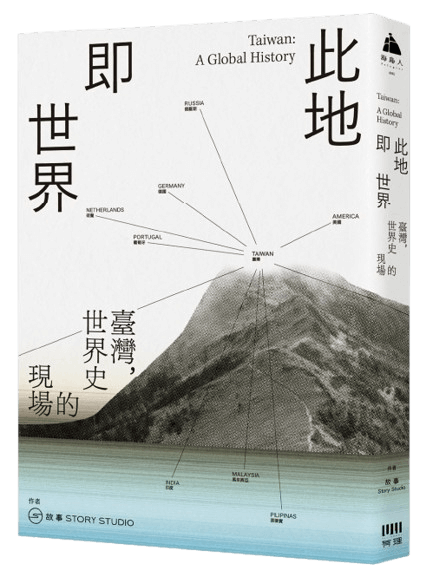
本文摘錄自《此地即世界:臺灣,世界史的現場》的〈臺南可果美|感謝日本搶贏俄羅斯的漁場,臺灣開始種番茄了:番茄醬與茄汁罐頭的百年史〉篇章/作者:廖品硯 & 故事StoryStudio著.有理文化出版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